稳定币超 2000 亿美金:美元占了 99%,人民币能分杯羹不?
我认为短期来看,美元的颓势是比较确定的因素,至少短期内增持美元资产未必是明智选择,黄金仍有机会。
当前将稳定币的可匿名特性切换为基于账户或身份管理并非难事。这些政策对美元信用的伤害尚未停止,仍在持续,客观上为非美货币提供了机会。
2025年上半年,受极端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暴跌10.8%,创下1973年以来最差半年度表现,一度跌破100点,引发市场对美元稳定性和美债的普遍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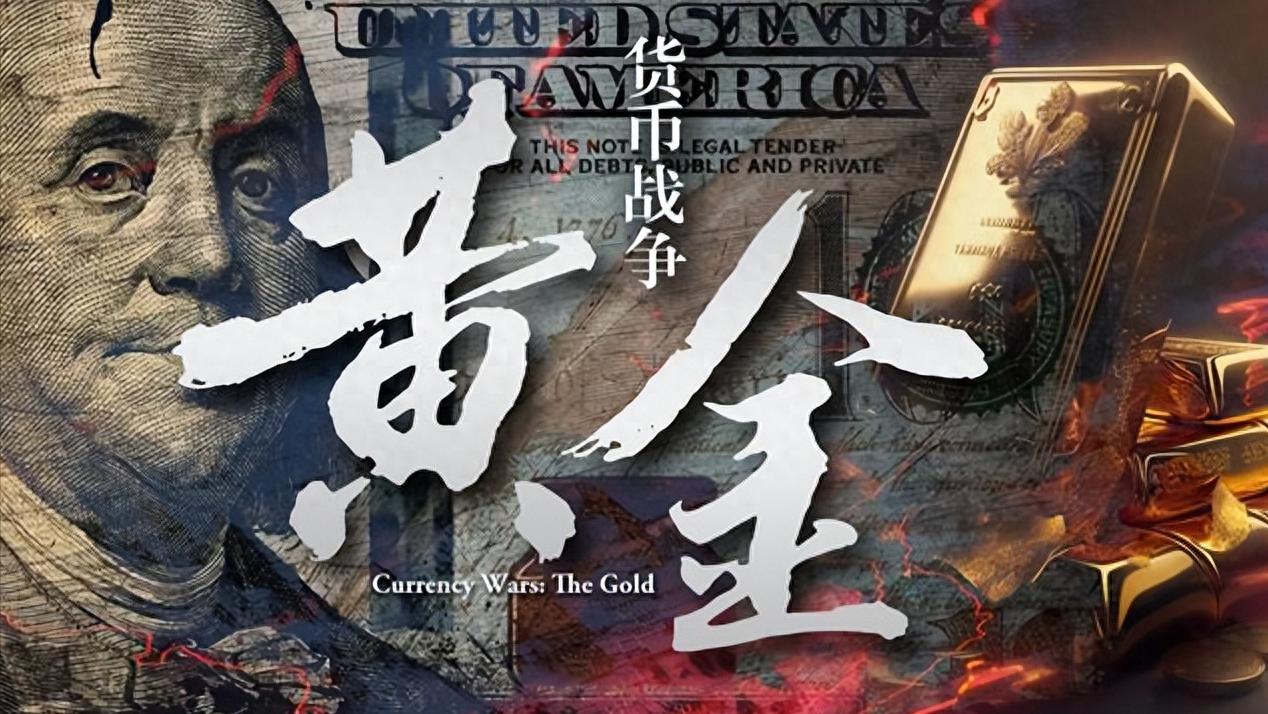
此轮美元调整与以往有何不同?全球货币格局深刻变革下,黄金再货币化趋势为何加强?稳定币发展是否由技术主导?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为何需着重发展直接融资?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将解读美元、黄金、稳定币与人民币的近期波动,分析全球货币体系变革中的新机遇。
一切需从美国近半年的系列政策说起。无论是美元、黄金还是当前热议的稳定币,其核心逻辑均与美国政策动向密切相关。
以美元指数为例,前六个月跌幅达10%,创1973年以来最差年初表现。市场普遍认为美元走弱不可避免,但这一趋势的时间区间(未来一年、五年或更长期)仍存疑问。
美元存在多次强弱周期,本轮超级强美元周期始于2011年初。过去十余年虽有调整(如2017年美元指数下跌10%),但调整时间短(2018年即企稳)。
当前讨论的美元调整或为长期、大幅调整,因本轮调整不仅受经济周期影响,更叠加结构性因素:美国政策导致全球贸易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重置、政府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引发信用担忧、政府债务在高利率环境下的可持续性存疑。
尽管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暴跌10.8%,但仍维持在100左右,仍属强美元区间(历史上美元趋势性走弱需跌破90,甚至80)。目前美元负面因素尚未根本逆转。
美国政府政策主观上加剧了美元弱势。特朗普偏好弱美元,上一任期曾多次批评欧央行实施零利率、负利率政策,呼吁美联储效仿。当前美元跌幅近11%,可视为其“得偿所愿”。
今年美元走弱的关键背景是“美国例外论”破产。2022年美联储紧缩周期中,市场预期美国经济衰退未兑现。
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贸易、移民及政府改革政策引发市场混乱,“特朗普交易”逆转成“特朗普衰退预期”。
尽管美国通胀、就业、增长等硬指标表现尚可,衰退风险边际上升但总体偏低,经济放缓已成定局。若经济放缓、就业恶化,美联储大概率降息,美元或进一步走弱。
关于美联储独立性受特朗普影响的问题,从其首个任期表现看,美联储“嘴硬腰软”。2019年7月31日起,美联储以“特朗普关税政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等外部风险为由,连续三次降息(当时美国经济、通胀、金融均无显著问题)。
当前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矛盾加剧,特朗普及政府官员频繁干预货币政策,动摇了自1980年代以来支撑美元国际信誉的美联储独立性基础,对美元信用伤害显著。
外界对特朗普政策的预期在其当选前后发生微妙变化,部分专业人士认为未来5-15年美元可能失去储备货币地位。
但历史经验显示,美元地位仍较稳固——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地位一度下降,1990年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各国通过积累外汇储备增强自保能力,美元重要性回升(占比从50%升至70%以上)。
后因美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时“大水漫灌”及美元武器化,信用受损,重要性再度下降。
美元信用受质疑时,黄金的连带反应值得关注。普通投资者关心“下半年应减持美元还是黄金”,业内亦讨论黄金再货币化进程。
短期看,美元颓势确定:若美国经济放缓,美联储大概率降息(利空美元);特朗普持续挥舞关税大棒,或再现极端波动。
需注意,历史上贸易摩擦升级时美元常因避险升值,但此轮因美国“单挑全球”、改变多边贸易规则,美元信誉受损反贬值,下半年美元仍可能调整。至少短期内增持美元资产未必明智,黄金仍有机会。
美国政策对美元信用的伤害体现在三方面:内外均衡冲突时“先内后外”,牺牲外部利益;政策“大进大出”产生强溢出效应,加剧其他国家经济周期错位;滥用美元武器化,对友好国家实施“长臂管辖”。
在此背景下,黄金再货币化表现为各国通过增加实物储备资产增强国际清偿能力。欧洲央行报告显示,2024年黄金在国际储备资产中占比20%,超过欧元(16%),成为仅次于美元(46%)的第二大国际储备资产(2022-2024年央行购金对金价形成重要支撑)。
当前金价高企削弱饰品性价比,但投资属性对私人部门仍具吸引力,央行储备多元化与私人资产配置两股力量共同支撑黄金需求。
美元走弱意味着非美货币对美元普遍升值(如2025年上半年欧元对美元涨14%、英镑涨9%)。欧洲担忧欧元过度升值冲击出口(欧洲贸易依存度高,叠加全球贸易紧张,汇率超调或造成双重打击)。
亚洲地区(如中国台湾)因本地投资者大量配置未对冲的美元资产,在美元趋势性贬值预期下集中对冲,导致新台币3天内升值10%,类似风险值得关注。
稳定币近期热议源于多重因素:比特币经历多轮调整(2023年硅谷银行事件致其市值缩水40%),当前稳定币规模超2000亿美元;稳定币第一股SKO上市表现良好;美国及中国香港推进稳定币监管立法;陆家嘴论坛宣布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
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背景下,中国央行数字货币(中心化)曾处领先地位,美国则在央行数字货币推进上“议而不决”,转而关注稳定币(加密货币范畴)。
当前稳定币市场90%以上份额由USDT、USDC(挂钩美元)占据,99%稳定币与美元挂钩。美国推进稳定币监管可视为“招安”行为。
关于人民币稳定币,若在香港发行并涉及跨境流动,需解决链上与链下对接问题。稳定币“占有即拥有、支付即结算”的匿名特性与内地管理逻辑存在差异,但技术上或可通过区块链技术调整(如将可匿名切换为基于账户/身份管理)实现对接。
例如,2025年6月内地与香港开通的跨境支付通业务使用2010年开发的快速支付系统(实时到账、零手续费),2018年深圳试点的湾区贸易融资区块链平台亦验证了区块链技术的可行性。
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关系更多是技术路径差异。稳定币所用的代币化、通证化技术并非唯一,现实中存在其他可并行的支付技术(未来可能出现更优技术)。
需避免将稳定币“神化”,认为其可实现货币国际化“弯道超车”——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多年,但人民币国际化指标波动与数字货币无直接关联。监管、实业及投资者需保持理性,避免概念炒作。
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挑战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效应”与“路径依赖”(传统货币使用惯性难改)。历史上美国GDP超英国后,美元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才全面取代英镑。
当前机遇在于美国政策持续损害美元信用,为非美货币提供空间。
中国需应对的挑战包括:经济结构性转型(经济强则货币强,资产吸引力是基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与国际接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需对接);发展直接融资(美国直接融资占比80%,其中超半数为债券融资;中国债券市场以国债、地方债、金融债为主,企业信用债占比低,信用评级制度与国际差异制约融资效率);应对全球经济碎片化、“去风险化”及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